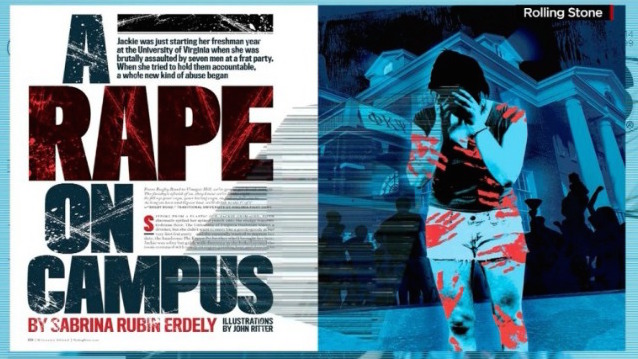編者按:記者該如何判斷線人說沒說實話呢?《滾石》雜誌去年11月的校園強姦案報道成了失敗案例,正是因為記者未經證實就輕信所謂受害者的敘述。非洲調查報道中心網絡(African Network of Centers for Investigative Reporting)的法律顧問Heinrich Böhmke回顧此事件,提醒記者應該多參考法律規範,即使信源的敘述很有說服力,語氣沉穩,前後說法也一致,也要以嚴格標準判斷其可信度。
編者按:記者該如何判斷線人說沒說實話呢?《滾石》雜誌去年11月的校園強姦案報道成了失敗案例,正是因為記者未經證實就輕信所謂受害者的敘述。非洲調查報道中心網絡(African Network of Centers for Investigative Reporting)的法律顧問Heinrich Böhmke回顧此事件,提醒記者應該多參考法律規範,即使信源的敘述很有說服力,語氣沉穩,前後說法也一致,也要以嚴格標準判斷其可信度。
《滾石》雜誌的編輯Sean Woods和其他同行一樣,最不想接到記者的認錯電話,但這樣的事還是在2014年12月發生了。《滾石》的一位記者告訴他自己現在一定要站出來,對所寫的報道負責。這篇報道揭發了一起可怕的校園強姦案,嫌疑人是弗吉尼亞大學兄弟會的男生。
報道不僅刷新了這本經典雜誌的閱讀量,還讓全國上下一片嘩然。原因很簡單。報道敘述了一位年輕女孩被強姦的經歷,她控訴約會對象引誘自己到兄弟會的一處房子,致使她在地板碎玻璃上被七個兄弟會新成員輪姦。報道所採取的立場是:受害者的經歷代表了女學生在美國校園遭遇的“風氣”。而大學回應時採取辯護的口吻,帶搭不理,更加縱容了這樣令人髮指的罪行。
Sabrina Erdely是《滾石》的資深記者。她的報道《一起校園強姦案》發表前經過了事實校對員、編輯和法律顧問的三重審核。但其他作者,尤其《華盛頓郵報》的記者,毫不費力地指出了報道的缺陷:往好里說,這篇報道算得上核心主張完整,但是事實片面、虛假;中肯地說,Erdely輕信了一位渴望吸引關注的青少年,只要有基本的調查報道知識就能發現她敘述的破綻。往壞了說,受害人Jackie的敘述本來就是一場荒謬的騙局。Erdely報道這個事件,只是因為這和她對大學生“富二代”行為方式的荒誕想象相契合。如Cathy Young所說,文章作者“特別熱衷於鼓吹,像信奉宗教一樣信任強姦指控”。

沒過多久,這篇報道在美國報紙和博客上被批得體無完膚。《滾石》聯繫了哥倫比亞新聞學院的院長Steve Coll,簡單明了地向他介紹了情況。2015年4月初,Steve Coll發表評論文章。他發現,記者和編輯過於信任單一匿名信源,即受害女孩Jackie 。記者和編輯對她的情緒特別小心,也沒多加思考。《滾石》雜誌同意,調查的範圍、甚至問什麼問題都由Jackie說了算。
Erdely錯在沒去求證關鍵事實,例如被控的強姦犯是否真有其人,Jackie對朋友同一時間的敘述與她採訪所說是否相符。她違背的媒體準則還不止這些。華盛頓郵報的記者將這篇報道稱作“一場無底的騙局”,因為Erdely和她的編輯不僅錯引了對話,也沒有給嫌疑人回應或否認這些嚴重指控的機會。
Coll的文章激發了不少頗有見地的解讀,主要關注兩個方面:敘事性新聞的陷阱在哪裡?報道在哪些地方沒有做好而使專業新聞蒙羞?對《滾石》的討伐聲中,人們也意識到此事件也為整個新聞行業提供了一次學習的機會。Erdely報道中的一些問題只有她自己會犯,而且有故意的嫌疑,但其他錯誤也是許多新聞從業者常犯的。報道有一個錯誤沒有引起足夠注意:因為Jackie複述的故事很連貫,而且她自己表現得很“自信”,所以作者認為她更可信了。許多新聞記者曾掉進這兩個陷阱。
Coll提出,Erdely“曾因為Jackie提供的細節過於生動而有過‘一絲懷疑’,比如砸爛的桌子上的碎玻璃。但Jackie‘很自信,且敘述前後一致’。”Erdely在Slate的採訪中再次提到了Jackie敘述的高度連貫性,她因此相信了Jackie。她回憶道,每次採訪中,Jackie說的所有細節都是一致的。
做事實校對的人花了四個小時打電話校對Jackie的說法。他也對Jackie生動、連貫的陳述印象深刻。“她不僅僅是在回答‘對對對’,而是在糾正我。”
因為一個故事前後沒有出入就認為它可信,調查報道就會在陳述證據時犯錯。醜聞揭發和法律業相比,是一個年輕的行當。記者們最好非常小心,可以參考法律界用來判斷證詞是否一致的“排除規則”,也來制定一條規則。和常識不同的是,一個證人重複他在之前場合作出指控,並不能提升敘述的可信度。因為這個證人很可能是在持續撒謊或是說真話。持續性本身並不能說明敘述內容是否有操縱的嫌疑。
當然,如果一個證人有編造事實的嫌疑,前後證詞的連貫性就是最有力的反駁。事件剛發生時的證詞也很重要。但法官和陪審團通常無需得知原告此後是否複述了控訴細節。這是因為在邏輯上,自證是沒法證明可信度的。
前後敘述一致並不能提高可信度,而敘述不一致確實能證明證人不可信。Jackie的敘述中當然有明顯不一致的地方,但Erdely並沒有努力挖掘它們。
衡量信源誠實與否,態度是另一個不靠譜的參數。Erdely從Jackie的“自信”中判斷出她是否在說實話的準確幾率,只比扔硬幣稍微大一點。一個人是自信還是靦腆並不代表什麼。Jackie在對話中的自信顯然提升了她在Erdely心中的可信度,而在另一些場合中Jackie表現的害怕和沉默也起到了相同效果。這說明把態度作為誠實與否的客觀標準是不可靠的。
但這不是說態度不重要。經驗豐富的記者往往對一個故事有“第六感”。這種感覺來自於採訪對象的眼淚或是微笑,他們直白的講述方式,來自於合作、讓步以及像真誠這樣難以捉摸的品質。然而最嚴謹的記者,不會僅憑態度就給採訪對象送上真誠的花環。即使記者沒有像法庭審判那樣分析他們的採信標準,他們也會檢查敘述是否存在矛盾、觀察是否可靠、是否有偏見。他們嚴肅思考過指控的合理性,並尋找證據證實違背常識的敘述。以上這些,再加上好的態度,記者在調查報道的反覆驗證里才能得出:這個信源是可信的“感覺”。
如果僅憑對方悲傷啜泣、眼神沉穩或者握手熱情這些跡象來判斷他/她是否真誠,那麼誤判的風險很高。那這樣的報道可能被刻板印象所控制,淪為通俗心理學調查,或者像Erdely一樣以偏見來核實事實。
調查報道本身就容易引發爭議。如果調查目標重要、資料豐富、報道風險大,就會激起很多方面不約而同、帶有偏見的巨大反應,報道也因此受到影響。一篇報道的影響越大,那些憤怒的呼聲就越強烈,律師的聲明就越義正言辭,一些錙銖必較的評論家就越容易站在道德高點發表評論。在文章發表前事先嚴謹細緻地檢查,這樣總比在話題升溫之後,讓對手手握把柄、吹毛求疵好得多。Coll的報道評論提到了不少新實用建議,能幫記者避免犯類似的錯,不至於打認錯電話。此外,經典法律書里也有許多好內容,記者可以參考涉及證據的內容,從多角度看如何判斷信源的可信度。
 Heinrich Böhmke是非洲調查報道中心網絡(African Network of Centers for Investigative Reporting)的顧問。他是南非專業技能研究所(Specialised Skills Institute of South Africa)的培訓師和主任。他曾調查舉報過貪污和性侵犯案件。
Heinrich Böhmke是非洲調查報道中心網絡(African Network of Centers for Investigative Reporting)的顧問。他是南非專業技能研究所(Specialised Skills Institute of South Africa)的培訓師和主任。他曾調查舉報過貪污和性侵犯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