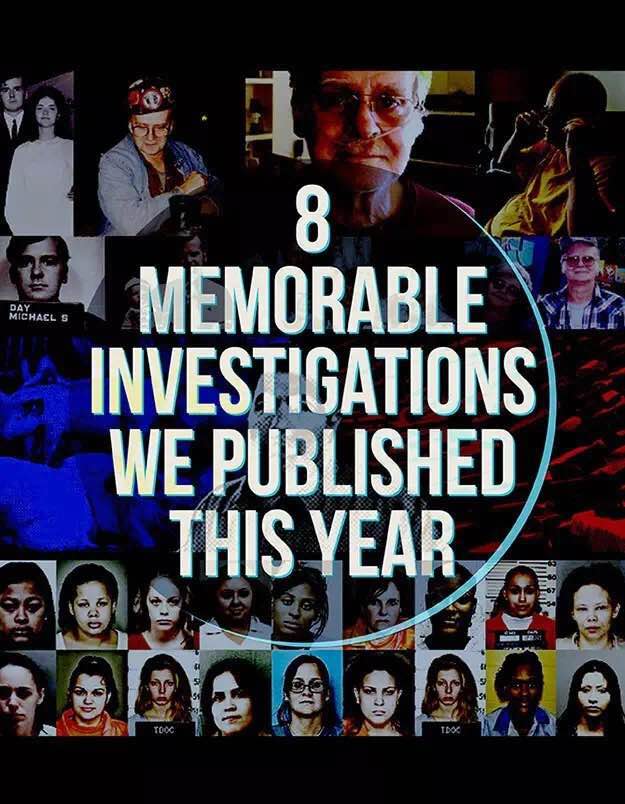還記得深度君之前分享過的《新聞界網紅Buzzfeed:我們也做調查報道,而且還不錯》的文章嗎?(戳標題即可查看)以視頻和輕鬆內容著稱的Buzzfeed做了不少優質調查報道,包括揭露網球賭球醜聞的調查,美國外勞項目中不公平待遇的報道等,讓人們意識到:深度報道也可以在新媒體獲得一席之地。
深度君經授權轉載刺蝟公社與BuzzFeed深度調查部主編Mark Schoofs的對話,看Buzzfeed如何看待深度報道與新媒體運營的結合、調查記者專業品質等(標題和開頭有刪改)。大家還可參考ProPublica的經驗《ProPublica:做數字時代的深度報道,建立模式是關鍵》。

BuzzFeed深度調查部成立之後第一年重要報道匯總
對話Mark Schoof
調查報道可以存在於任何一類媒體
(原採訪以英文進行,為方便閱讀,以下為譯為中文後的採訪實錄)
C=刺蝟公社
M=Mark Schoofs(BuzzFeed深度調查部主編)
C:在加入BuzzFeed之前,你有豐富的在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等等非常知名的傳統媒體工作的經歷,那麼當時為什麼願意加入BuzzFeed這樣一個以“輕新聞”甚至是“搞笑新聞”而聞名的新媒體做深度調查部的主編呢?
M:嗯,其實在加入BuzzFeed時,我正在ProPublica(美國一個關注公眾利益的調查性數字媒體)做編輯,我很滿意自己的那份工作,因此並沒有找工作的打算。其實當時,我連BuzzFeed是什麼都不知道,所以知道消息之後打算去和他們見面也純粹是想去了解了解這個我從來都沒聽說過的新媒體,長長見識。
那時候的BuzzFeed還沒有現在做得這麼大、這麼全面,而且發布的嚴肅意義上的新聞報道很少很少。但從他們當時拿給我看的幾篇此前發表過的深度報道來看,質量非常高,我能真切地感覺到他們正在往這個方向所做的努力和嘗試、以及他們構建深度調查部這個想法的前景——就像那句諺語說的,“一堆石塊在多數人只是一堆石塊,但在有些人看來卻是一座宏偉的教堂”,對吧。(笑)
於是,我愈發意識到這對我來說將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我可以從零開始組建一個全新的深度調查報道團隊,而且BuzzFeed作為一個很大的網絡媒體平台,也完全可以提供充足的資源支持。我當時就覺得,如果自己拒絕了這個機會,之後一定會後悔的。於是,我就不顧一切地加入了——而事實也證明,這是我這輩子所做過的最棒的一份工作,沒有之一。

BuzzFeed深度調查部主編Mark Schoofs
C:對於你來說,在BuzzFeed做深度調查報道和之前在傳統媒體有什麼不同嗎?
M:我要對你這個問題本身提出強烈抗議,強!烈!抗!議!我認為這兩者之間根本沒有什麼不同……
首先,我認為其實在調查報道這一塊,BuzzFeed本質上其實還是一個最最傳統的媒體。我們做些什麼呢?兩點:一,去發掘一個尚且不為人知的真實故事;二,想辦法以震撼心靈的方式去呈現它。如果你去看一看我們發布的調查報道,你會發現它其實並沒有特別地酷炫,甚至還沒《紐約時報》的文章里包含的網絡元素多。我們的目標是在質量上保持最好,然後在形式上保持簡潔,因為如果插入太多花哨的元素,在手機上的體驗就會受到影響,而這是萬萬不可的。
所以說,我真的覺得我們是很“傳統”的,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們做的還是一樣的事——發現故事,尋找信源,採訪,查證,分析數據和信息……這無關你在哪兒,你在什麼機構,調查報道的實質一直都是這樣。
C:在中國,媒體界內有一種說法是深度調查報道只有在傳統媒體才能更好地生存,因為傳統媒體掌握着更優質的資源和更專業的記者,更能保證報道的質量。就我推測,你不同意這種觀點?
M:你猜得對,這我絕對不能同意。什麼人才能稱得上是一個“專業”的記者?我不知道在這件事情的認知上中美之間有沒有什麼文化上的差異——畢竟你知道的,美國人的想法都比較奇葩(笑)——但至少在我看來,專業的記者就是任何一個認真採訪、查證,然後坐下來認真寫字的人。你的名聲和影響力是你所寫文章的高質量而日積月累來的,你可以是個寫博客的,也可以是個自由撰稿人,只要你的作品準確、公正,那你就是一個專業的記者,這無關你的學歷,也無關你到底是在傳統媒體還是數字媒體工作。
C:你認為對於深度調查報道部門來說,未來主要的承載媒體是哪些?
M:從理論上來講,深度調查報道可以存在於任何一類媒體,只要報道的質量能夠保證,記者足夠專業。但從現實的角度出發,主要可能是三類:一類是老牌優秀的傳統媒體,一類是關注公眾利益的非盈利組織,例如ProPublica,還有一類就是像BuzzFeed這樣的網絡新媒體。
不過,對於新媒體來說,深度調查部將只能作為其發展版圖的一部分,而非全部。因為優秀的調查報道當然可以為媒體帶來知名度和可信度,並由此帶來盈利,但總體上來看,調查報道依然存在生產周期長、成本大回報低,甚至還有可能因為報道而面臨打官司的危險,因此新媒體必須同時要有其他內容的生產幫助盈利,然後才可以從中撥出一部分來為調查報道提供充足的資金和資源支持。
手機讓閱讀長篇更流暢
深度報道讀者並未減少
C:現在手機改變了我們的閱讀習慣,很多人直接從Facebook或者WeChat上面看新聞,不少媒體也試圖把文章寫得更加短小簡潔,以適應手機上的呈現。對此,你怎麼看?你覺得追求簡短、多圖、小標題化是未來新聞呈現的一種正確的方向嗎?
M:事實上我認為對於深度調查報道來說,智能手機的普及反而是一件好事。首先,你可以只用一隻手拿着手機,用同一隻手的大拇指操控閱讀節奏,它的整個體驗非常舒服自然,也會讓你在看文章的時候特別流暢。這其實是更方便人們閱讀敘述性的文章了,換句話說,一篇深度稿子可能在手機上閱讀地更流暢而且舒服了。

雖然我也覺得偶爾用一些加小標題的總結性的短文,或者是短視頻等等作為深度稿件的引子發布在Facebook之類的平台是個不錯的傳播手段,因為它更能幫助你去發現和接觸你的潛在用戶。
但毫無疑問,現在的人們還是願意認真閱讀一篇長篇的優質深度稿的。比如,我們前不久剛發表的揭露世界頂級網球組織操縱比賽的內幕深度調查,就收穫了遠超過100萬的閱讀數,但那篇文章並不短,應該說是,非常的長,它基本算是我們寫過的最長的稿子之一了,但樂意去閱讀的人依然很多。
更重要的是,即使我們在故事的開頭對整件事做出了精鍊的概括性的描述,但是還是有很多人去看了後面細細展開的故事性的描寫和敘述,我很清楚這一點,因為不僅有不少人專門來跟我們講他們對於後面的敘述的想法,通過後台數據,我們也可以看得到人們閱讀到了整篇文章的大致哪個位置。
而我們的讀者的閱讀來源,80%都是手機——然而我其實並不相信真的能有20%的人會真的用電腦看,我估計他們恰好在電腦看到了文章於是想發送鏈到手機上留作以後再看吧。所以,我認為智能手機其實是給長篇深度調查報道打了一針強心劑的。人們現在會在手機上看一百多頁的電子書,所以只要他們對深度感興趣,他們當然能方便地在手機上看一篇幾千字的調查報道。你難道不這樣覺得嗎?
C:嗯,可能確實如此。但現在在中國,很多媒體人感到由於新媒體的衝擊和傳統媒體的日漸衰落,調查報道的讀者減少了,甚至很多此前從事深度調查報道的記者們也擔心調查報道越來越難做,紛紛轉行……在美國是否也有這種情況?在你看來,美國的調查報道讀者是減少了,還是沒有很大變化?
M:我手裡沒有現成的統計數據,但我的感覺是,現在在美國,調查報道的讀者群不是在縮水,而是在增長。尤其是現在,美國正值總統大選的瘋狂時期,人們極度渴求信息——不僅僅是關於希拉里·克林頓、唐納德·特朗普、泰德·克魯茲還有伯尼·桑德斯這些總統候選者的資訊,還包括他們在競選中提到的社會問題的相關信息。
事實上美國人都很清楚總統大選並非絕對公平,掌握大把鈔票的人所能攫取到的有利資源是普通人遠遠無法比擬的,也正因為如此,人們更是非常想搞清楚這中間的邏輯。
再比如,最近因為警察誤殺黑人平民的一些列事件,“Black Lifes Matters”(“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成為美國人關注的焦點之一。這時候,調查報道所能做的就絕不僅是加入到觀點性的論戰中,而是通過嚴肅可靠的報道和分析,釐清問題形成的原因,幫助人們了解所在城市和美國政府會如何處理這些非常重要的司法不公問題。
所以,我認為調查報道的讀者從來都沒有減少,更確切地說,正是現在這個時代,我們正極度需要這些真正嚴謹的深度調查新聞人,來向受眾呈現社會事件中千絲萬縷的複雜關係和邏輯,對於受眾來說,這些客觀深度的報道甚至比媒體人觀點性的評論更為重要。
雖然客觀地來講我對中國了解甚少,我只去過中國一次,因此不敢依仗自己的無知妄加評論,但在至少從需求上來看,我不信中國會與美國有太大的不同——雖然我們可能有着不同的文化和社會風俗,但作為人類,我們對於自己都是對複雜的事物充滿好奇心的,難道不是嗎?這就是調查報道之所以存在的根源啊。
C:此前BuzzFeed以搞笑和網絡熱門輕新聞為主,用戶閱讀喜好可能比較垂直。這些用戶會與深度調查板塊的用戶有較大重合嗎?現在深度調查板塊的讀者主要是怎樣的人群?
M:肯定是有所重合的。總體上來看,我們的讀者比其他媒體的調查報道讀者偏年輕,同時女性也比男性偏多,中年男性也佔了不低的比例。但是,這個問題還是不能一概而論,因為我們發表的調查文章涉及非常不同的話題和領域,因此不同的調查報道可能完全吸引來的是不同的人群。以我們之前發表過的兩篇報道為例:其中一篇揭露了某網球組織操縱比賽結果的內幕,其讀者也可能多是那些原本就對網球運動比較關注的人;而另外一篇則揭露了美國最大的一家商業性的家庭寄養中介公司為了盈利,將孤兒交付給有犯罪前科或虐童傾向的家庭寄養的情況,這就可能帶來於上一篇完全不同的讀者群體。
C:既然如此,有沒有想過通過精準定位某個讀者群體的方式推廣個別稿件?
M:我們會這麼做,但其實大多不是出於商業推廣的目的,而是專門去向那些對現狀有改變能力的人進行推薦。我們一貫的做法是,如果我們的某篇調查所揭露社會問題可以通過新的法律的建立或完善得到解決,我們就一定會盡一切辦法——不管是通過直接打電話還是發郵件還是通過社交網站聯繫的方式——把我們的文章推薦給當地所有相關的立法委員。我們不會要求他們做什麼,但至少要確保他們了解我們調查的結果,這樣就更有可能對當下的社會問題做出改善。
(*刺蝟君按:事實上,剛剛Mark提到的那兩篇關於網球組織內幕和家庭寄養中介公司的不負責行為,分別推動了網球界對反腐項目的獨立評估體系的建立以及美國參議院對家庭寄養制度實施情況的進一步調查)

BuzzFeed深度調查部對於網球組織內幕交易的報道,與BBC合作發表
優秀的調查記者
大膽敲門,細心求證
C:在你看來,什麼樣的人能成為一名好的深度調查報道記者?
M:你首先要有一個發現不當行為或者說是負面問題的嗅覺,因為調查新聞永遠不是去誇一個人有多麼多麼的好,而是去指出錯誤,揭露問題。同時,你還要一定能堅持公平公正的職業操守,要專註於嚴謹公平地求證。
我們團隊的記者寫文章都要遵守一條規矩,我們稱其作“No Surprises”(“無詫異”)準則。這個“no surprises”,指的是被報道者在看到我們所發表的調查報道後,不會對任何我們在文中所提到的信息感到詫異——而這也就意味着,如果我們想要報道關於某人的貪污行為,我們就一定會在寫文章之前通過各種方式聯繫到這位當事人,向他說明我們將要撰寫的稿件以及我們計劃寫入文章里的關於他的任何事實或信息,以給他最後一次闡述自己一方事實或觀點的辯駁機會。
只有這樣,在文章發表前讓多方知情,並且不無視任何一方的意見或闡釋,我們之後才可以在報道中舉出多方言論或證據展現真偽。也只有這樣,我們的報道才能做到公平公正、可信可靠。我描述得還清楚嗎?
C:也就是說一名好的調查報道記者,不僅要有發現問題的熱情,還必須要有一個開放的思想和心態,客觀平等地對待每一位被報道者,接受一切真相或事實的可能性?
M:沒錯,一定要有一個開放的心態,有濃烈好奇心的同時,必須還要有真誠的求證欲。不管從目前你所掌握的信息來看,被報道者做了多麼可怕的事或是犯了多麼嚴重的錯誤,你都要把它當做是一個理論性的假設,而你所要做的,就是盡一切可能,去驗證這個假設的真偽——並在採訪和調查同時,時刻相信這個假設隨時有被新的證據或信息推翻的可能性。當然,一旦你在充分的調查之後確信自己已經掌握了充足的證據來證明整件事,你又必須要有足夠的勇氣把它講出來而毫不畏懼。
C:最後一個問題。你對於最近獲得奧斯卡最佳影片獎的電影“Spotlight”(《聚焦》)怎麼看?人們說這部電影是獻給調查記者們的禮物。
M:我簡直太!愛!這部電影了。(認真篤定臉)至少它沒有落入傳統好萊塢電影的俗套——你看,那女記者最後也沒有跟男記者墮入愛河呢!
C:(笑)那麼你認為這部電影真實地反映了調查報道記者們的日常工作狀態嗎?
M:是的,影片雖然描述的是記者對於神職人員性侵兒童一事的調查報道,但卻把中心放在了記者們一路披荊斬棘的經歷而非性侵事件本身上,所以我說這是一部關於深度調查報道的電影。
我還記得當那個男記者知道自己能拿到文件的時候,激動地飛奔去法庭那一幕……那種感覺真的太……真的是是每一個調查報道記者都切身經歷過的體驗。又或者是,當那個女記者終於敲開了神父的門後,神父直截了當地對她說“哦是的,我性侵了那些孩子們”時,女記者的那種難以置信的驚詫——這也是能讓一位調查記者感同身受的經歷。

很多時候,採訪對象會向我們坦白很多他們從來沒對任何人說過的話,他們的坦然有時候真的會令我們根本連想不敢想。對於一個記者來說,最糟糕、最最糟糕的想法就是:“我還是別給那人打電話了,他肯定不會接受採訪的”。你怎麼知道不會?在調查報道中,萬事皆有可能。
還有一個,就是記者們一次次地翻有着神父和教區信息的教會名錄的時候,他們發現了把涉案神父一個一個鑒別出來的方法——這也是在調查報道中經常會有的體驗,往往是一開始在尋找某一樣東西,但在進行極度深入的調查和全方位的掌握後,你對資料的爛熟於心能夠能夠為你打開一條發現證據的新的渠道,一種你從未想到過的渠道。這些細節,都是調查新聞記者們在實際工作過程中會遇到的最大的共鳴。
采寫/郭雅楠
深度網編輯/周煒樂
原文來源:刺蝟公社
採訪原文:《調查報道記者們,這仍是我們的黃金時代|獨家對話BuzzFeed深度調查部主編》
採訪手記:《約訪BuzzFeed調查報道主編:一場越洋對話始末|前傳 & 後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