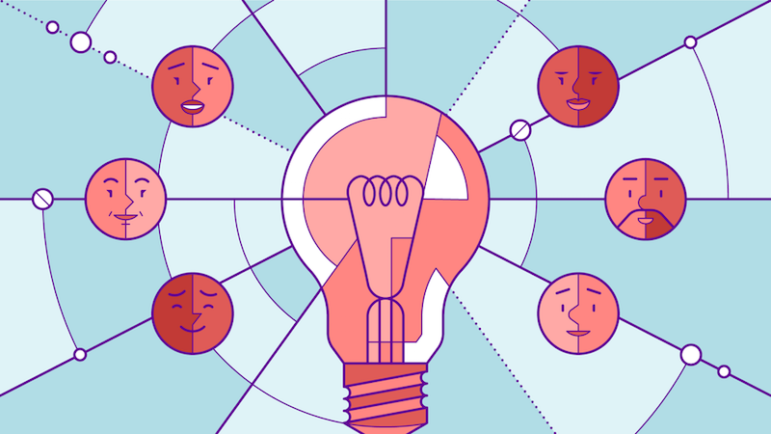
2018 年,新聞網站 Reveal 的記者 Will Carless 和 Aaron Sankin 開始準備一項關於白人民族主義者如何看待福克斯新聞(Fox News)主持人 Tucker Carlson 的報道。兩位記者找到了一個新成立的志願者組織“仇恨偵探團”(Hate Sleuths)來一起做調查。
伸出援手的仇恨偵探們有幾十位,他們深入了一些網絡留言板和社交媒體(如 4Chan 和 Gab),搜索提到 Carlson 的條目,並將搜索結果分享給 Reveal,後者將其發表在了 Reveal 每周的“仇恨報告”(The Hate Report)新聞信里。Carless 是 Reveal 駐巴西的記者,他在之後對 Carlson 的訪問中 2018 年 12 月 7 日的“仇恨報告”—— 這份報告凝聚了志願者的貢獻,講述了 Carlson 以及極右媒體對他的“全力支持”。
這份報道源於仇恨偵探團參與的一個名為“美國新版仇恨面孔”的專題,由 Carless 和 Sankin 為調查新聞中心(the Center for Investigative Reporting)的 Reveal 平台所做。“偵探團”現在大約有 50 名成員。
Reveal 把與志願者組織的合作發展成了一個為期六個月的新聞實驗,名為“加入專題”(Join the Beat),作為“會員制求索項目”(the Membership Puzzle Project)下面的一個實踐社團(編註:“會員制求索項目”是一項研究會員制模型的公共研究項目)。隨着 Reveal 報道涵蓋的範圍越來越廣 —— 跨越了多個時區和學科 —— 他們想知道自己最熱情、最忠實的讀者們會不會伸出援手。
到目前為止,答案是肯定的。偵探團早前協助的 9 月 28 號的《仇恨報告》里,提到了一個反猶太食品的手機程序“KosChertified?”,這個程序會在極右的播客節目上做廣告。報道出街的一周後,《仇恨報告》發布了一則信息:蘋果把反猶太視頻的程序從蘋果商店撤下了。
“這樣我們就可以高效地克隆出更多的自己,去閱讀更多的材料、做更多的研究、聆聽更多的聲音。”卡萊斯表示。
把專題變成網絡
誠然,Reveal 的一招不會吃遍天下,但借用讀者的知識卻觸及到了專題報道的核心:尋找了解且關心議題的人,利用他們的信息來更好地進行報道。
“加入專題”的想法來自於媒體評論家、紐約大學副教授及會員制求索項目總監 Jay Rosen,他把這個創意有推向了新的階段:如果一個專題成為了一片網絡,記者應該怎麼更好地接入這個網絡,從而達成更高的質量、更深的信任和更強的讀者忠誠?

調查新聞中心的 Reveal 平台記者 Will Carless 和 Aaron Sankin 在《仇恨報告》新聞信中發布了招聘志願者的號召。
我們在 2018 年花了六個月的時間,與來自美國、加拿大、荷蘭和蘇格蘭的 10 位記者探討了這一話題。這些記者背景各有不同:使命感極強的新創媒體(例如蘇格蘭的 The Ferret 和加拿大的 The Discourse)、都市日報(《杜倫先驅太陽報》(The Durham Herald-Sun)和《多倫多星報》(Toronto Star))、南加州 KPCC 廣播電台(Southern California Public Radio/KPCC)和開創性的數碼組織 ArsTechnica,以及荷蘭的 De Correspondent,外加 Reveal 和 Technical.ly Baltimore。我召集了整個小組一起開了個視頻會議,進行了以下議程:
• 比較各自的進度;
• 大家彙報了各自的實驗結果,聆聽了一些嘉賓講座。比如我們邀請了 Terry Parris Jr. 給大家講述 ProPublica 是如何將讓讀者參與到一些基本報道和現場報道里,《達拉斯晨報》(Dallas Morning News)的 Hannah Wise 則演示了報紙訂戶的 Facebook 群組是如何增進聯繫的;
• 展開頭腦風暴,想一想如何邀請別人加入自己的專題調查和報道中(這一環節基本上以擔任或兩人小組來進行);
小組每兩周開一次會 —— 期間大家也會交換想法,並且跨越時區和我單對單地討論一些點子 —— 會上大家討論了如何邀請了解且關注議題的人一同加入、共同增進報道質量,也討論了其中的好處和困難。我們不僅學到了更多專題網絡的知識,還了解到建立實踐團體會遇到的現實狀況 —— 記者如果能花更多的時間,並且爭取到更多人支持“加入專題”,最後一定會取得更好的結果。Mathew Ingram 在《哥倫比亞新聞評論》(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里如此描述這次的項目:
“優秀記者總是會在報道時尋求讀者和專家的幫助,網絡 —— 尤其是社交網絡 —— 讓這種‘眾籌’更加輕鬆。不過從新聞報道的角度來說,記者和媒體必須清楚了解自己想從眾籌中獲得什麼信息,也要清楚如何構建這些信息,這些工作在報道導開始前就需要花上大量的功夫。”
我們的合作媒體 De Correspondent 的參與者 Maite Vermeulen 正準備移居到尼日利亞的拉格斯,將那裡作為她的移民專題的根據地。大家在故事、聯絡人和參考書籍方面給了她不少建議,她也在這些建議的基礎上繼續深挖。

“與我一起旅行,問出你的問題,”De Correspodent 記者 Maite Vermeulen 這麼邀請平台成員。她正準備搬到尼日利亞,探索移民歐洲的話題。
Vermeulen 之後接着邀請其他成員加入,促成了大家和她採訪過的一位移民對話,探討為何這些移民會在歐盟嚴令禁止之下,依舊義無反顧地前往歐洲。她另外還有一個故事,講的是伏都教祭司和伏都教詛咒在販賣人口中扮演的角色,報道這個故事時,她和她的同事們也一起集思廣益,如何邀請更多有相關經歷的人一起討論這個主題。
De Correspondent 發布了這篇伏都教的報道之後,網站上一位名叫 Maria 的網友表示,自己就是一名伏都教祭司,並且幫助過人口販賣的受害者。“我以前可以、現在也能用宗教儀式和治療幫他們擺脫可怕的奴隸生活。但在過去荷蘭人並不在乎,現在也是如此。”這段留言引發了讀者和記者之間的漫長討論,大家確認了瑪麗亞伏都教祭司身分的專業性,希望她能舉出幾個例子,說一下自己是怎麼幫助荷蘭人口販賣受害者的。瑪麗亞在評論區事無巨細地解釋了她舉行的宗教儀式,也回答了其他讀者的問題。
Vermeulen 覺得,她的媒體平台能發起這樣的一次互動,主要是因為讀者自願付款成為會員,平台也將他們當成新聞的相關人士和參與者。不論是她向會員們解釋自己報道的方法,還是向會員們尋求意見,這都是她工作內容的一部分,並不是額外的事情。(De Correspondent 的記者必須花上至少 30% 的工作時間來跟會員和組織外的專家們互動)
“也許應該說,這正體現了新聞的特點,”Vermeulen 說,“你只要把它想成一組巨大的新聞來源就行了。”
讀者們知道什麼,我們又學到了什麼
這些想法並不是“加入專題”的首創。早在幾十年前,記者兼作家 Dan Gillmor 在報道硅谷新聞時,就已經將“讀者懂得比我多”這一思想奉為行為準則,並一直堅持至今。“互動新聞”已經成為新興的體系。ProPublica 就將這些方法作為他們發掘新聞的方法,而不是僅僅用在發布新聞上。
但專題網絡需要的是一種和“我發表、你評論”不同的方式。記者們醞釀或者開展報道時,向讀者會員或相關人士尋求建議。同時,回復這些網絡建議也是記者出產報道的步驟之一。
根據一些簡單調查和一些大型活動,我們收穫了這些心得:
新聞信是和鐵杆讀者溝通的最有效、最自然的方式
《仇恨報告》已經組織起了一個關注 Reveal 仇恨專題報道的社群,而仇恨偵探團的貢獻又讓他們的閱讀量和新聞信訂戶急速上升。ArsTechnica 記者 Eric Berger 創辦了《火箭報告》(The Rocket Report),作為“加入專題”的一份子,聚焦火箭發射行業。他很快就吸引了上千訂戶,其中有不少人響應 Berger 的號召,與他分享了很多相關的文章和研究鏈接。他也將這些鏈接分享給新聞信訂戶,並且附上提交鏈接者的帳戶名稱。

Eric Berger 和 ArsTechnica 發起聚焦火箭發射行業的《火箭報告》新聞信,邀請讀者分享相關文章的鏈接和信息。
加拿大溫哥華 The Discourse 的記者們創辦了一個聚焦山火解決方案的新聞信訂閱,並向讀者尋求建議。記者 Lauren Kaljur 形容交流過程“非常強大。任何時候你去問別人‘有什麼是你不知道的嗎’—— 誰都愛聽這句話。大家貢獻了很多資料,供我們構思。”
專題網絡的建立輕鬆簡單,只需要利用你的網站或者社交媒體
Technical.ly Baltimore 的 Stephen Babcock 會在每月的采編計劃公告(“下個月我們要報道這些主題”)里號召讀者們貢獻想法,最後收到的反響遠超預期,並至少醞釀出了一篇講馬里蘭州網絡安全的好文章。一個月後,《Technical.ly》把月度采編計劃公告里的號召擴展到了所有市場。
《The Toronto Star》的 Nicholas Keung 是一名報道移民專題的資深記者。他將報紙旗下創立已久的 Facebook 移民專頁改頭換面,重點幫助專頁的 1200 多名關注者提出他們的想法。這為專題報道開闢了新的天地,但其實早已有很多記者在吸引對報道有興趣的關注者,這些人也隨時準備好貢獻力量。
讀者可能不止想參與你的專題,還想跟你並肩作戰
蘇格蘭非營利調查新聞平台 The Ferret 採用的是合作模式,最初參與“加入專題”時聚焦環境報道,但後來發現讀者對問責報道的反響更大,尤其是蘇格蘭的主要報紙在這方面的進展其實已經舉步維艱。The Ferret 社群聯絡與創新總監 Rachel Hamada 表示,“現在正在想辦法讓環境專業人士也加入進來,我們的讀者也非常清楚地表達了這個需求 —— 例如回收、核能這些關鍵議題,他們都想獲得清晰、無偏見的信息。”
The Discourse 專註於讀者研究和社區聆聽,參與到“加入專題”時,專註在一些非常具體的主題上,例如環境和可持續發展。通過一些聆聽社區的講習和調查,The Discourse 的記者和管理層意識到,讀者們對特定地區報道更有興趣,尤其社區服務匱乏的問題。等到我們的實驗結束時,他們已經重新制定了報道這些社區利益的策略。
首席執行官兼創始人 Erin Millar 在回復讀者的新聞信里這麼說道:“我們發現,在我們最成功的故事背後,那些記者們在當地都紮根很深。我們加倍努力,植根於本土。”The Discourse 重新啟動了自己的計劃,聚焦在三個社區:安大略省的斯卡波羅(Scarborough)、卑詩省南部城市原住民社群、卑詩省科維昌谷地(Cowichan Valley)。點擊此處可以閱讀 The Discourser 全文。

記者 Lauren Kaljur 在向“加入專題”小組的報告中,分享了 The Discourse 策略根據成員反饋而轉變的軌跡。
“這真的就像一針解毒劑,媒體上的新聞讓人感到抽離或沮喪,”記者 Lauren Kaljur 描述她意識到了諮詢讀者和相關人士對報道早期的巨大作用、“頓悟”的那一刻,“它讓你更加明確了:這就是你想要的。”
為了支持專題報道和其他雙向交流,新聞操作系統需要升級
新聞的主要功能仍舊是收集、出版或廣播,並沒有參與到事件中,更像是附加作用。“加入專題”之所以會取得成功,來自於記者的同事們(編輯、其他記者、社交媒體專輯)的幫助:他們協助記者一起思考主題,幫忙解決後勤困難 —— 例如使用谷歌表格、ScreenDoor 或電子郵件來交流手上的讀者資源。有不少記者都頭疼沒有足夠的時間去處理網絡上的回復 —— 時間都糾結在 SurveyMonkey 或者谷歌表格中了 —— 更別說去對讀者分享的信息做出反饋了。
KPCC 的交通及通勤記者 Meghan McCarty Carino 在編輯部互動總監 Ashley Alvarado 的幫助下,定期使用美國公共媒體(American Public Media)的公共意見網絡(Public Insight Network)—— 這是登記成為新聞線索人士的數據庫。儘管有些疑問收到了數十條回答,但整理這些答案的工作量卻讓人難以應付。Carino 覺得參與式新聞還大有潛力可挖,尤其是將不同的專家和與消費者聯繫起來,這樣他們不光是和記者交流,相互之間還可以進行討論,創造更多的可能性。她說:“我覺得最大的阻礙還是常規的工作習慣 —— 想讓它真的有用,要花費不只是時間”,想要讓這些努力對報道產生核心作用,往往需要更多的付出。
De Correspondent 的 Vermeulen 的主要職責包括了和會員進行溝通,她也表示,自己還在想辦法構建出一個最效率的溝通渠道,而互動編輯的加入則幫了她大忙。
儘管大家對“加入專題”概念十分熱忱,但還是有一些記者遇到了困難,甚至闖進了死胡同 —— 不斷變化的任務、十萬火急的需求、管理讀者回復都會帶來挑戰。
“互動新聞”這個行業還沒有什麼嚴格的定義,但很多做這一行的都會從 Gather 網站獲取線人。Gather 是一項由廣場新聞中心(Agora Journalism Center)發起的合作項目,John S. 與 James L. Knight 基金會和 Democracy Fund 出資。還有很多人會去 Lenfest 學院、哈佛大學斯坦中心的網站以及 Yellow Brim 學習新聞信這個新方法。
儘管大家對“加入專題”概念十分熱忱,但還是有一些記者遇到了困難,甚至闖進了死胡同 —— 不斷變化的任務、十萬火急的需求、管理讀者回復都會帶來挑戰。《杜倫先驅太陽報》組建了一個 Facebook 小組,邀請社群成員和專家一起加入到“我的街道故事”—— 為期一年的調查中產化的項目。但住房記者 Zachery Eanes 被分配到了其他任務中,難以如願繼續在“加入專題”緊密地和城市居民保持聯繫。不過,無論最終是成功還是失敗,記者們都學到了東西。隨着實驗進入尾聲,大部分人都對專題網絡的好處都有所領悟。
Technical.ly Baltimore 的 Stephen Babcock 認為,“‘專題網絡’里的‘專題’並不是某一個主題領域,更像是一個群組。等你差不多確定了報道框架,這個群組裡的人就成為了你的資源,為你提供信息 —— 他們就是你的讀者,但同時又可以為你的工作做出貢獻。”
要有更多光
Reveal 的 Sankin 和 Carless 在《仇恨報告》的新聞信里,號召大家加入他們的專題,並以谷歌表格進行註冊。他們還在編輯和律師的幫助下,設下了“行車規定”,同時還經過篩選任命了一名協調員 —— 也是志願者 —— 幫忙組織並聯絡仇恨偵探團。
Carless 一開始並不看好與志願者合作,但他看了《仇恨報告》收到的第一批回復後,立刻就充滿了幹勁。申請註冊的人多種多樣:退休的圖書館管理員,想了解仇恨行為的 22 歲的年輕人,在加拿大研究同類話題的教授⋯⋯

Reveal 的 Will Carless 和 Aaron Sankin 利用谷歌表格收集申請,招募有心幫助他們報導仇恨專題的志願者。
來自三藩市的 Carolyn Knoll 也是一名支持者。她退休前在房地產行業做了十年的房產清算。她註冊之後被選為志願協調員。在與 Carless 和 Sankin 協商的基礎上,她負責和偵探團的一部分聯絡工作,並且提醒記者交稿日期,也會做一些其他組織性的任務 —— 志願者的角度和想法也能幫助記者和偵探團更好地合作。
Knoll 表示,這項工作並不會花太多時間(有時候一周會有幾個小時,有時候會更少),但足夠讓她實踐自己的參與精神,並且更加肯定 Reveal 所做的工作。退休後,她加入了和平隊,之後在夏威夷國家公園擔任志願者協調員 —— 正是這樣的經歷讓她能幫助 Reveal 去與仇恨偵探團這樣的志願者組織溝通。
有些人希望自己的聲音能得到聆聽,有些人無法出錢但想出力,也有像偵探團這樣的,渴望參與到更大的行動中。
為什麼要做志願者呢?Knoll 認為,仇恨偵探團的成員的背景多種多樣,但“我敢說他們所有人都對現在我們文化中的仇恨現象非常擔憂。他們還年輕,剛剛發現了《仇恨報告》,只是真心想幫忙。”
的確,社群成員加入、幫助新聞組織背後的原因各有不同,Stephanie Ho 和 Emily Goligoski 就在他們的文章《為什麼你的社群成員想幫你做新聞,以及你可以讓他們幫忙的 25 件事》深度探討了這個問題。有些人希望自己的聲音能得到聆聽,有些人無法出錢但想出力,也有像偵探團這樣的,渴望參與到更大的行動中。
Knoll 輔助 Reveal 的團隊處理後勤工作,包括一些備受矚目的熱門專題報道。Sankin 和 Carless 向偵探團布置任務以及大概所需時間。Knoll 則負責處理反饋、聯絡、截稿日期,並與其他組織溝通。
現在整個組織都已經人員齊備、各就各位,記者和志願者們相互之間越來越熟悉,也從對方的經驗和成果中互相成長,Carless 認為仇恨偵探團的作用在未來會更加重要。偵探團會接受申請公共記錄的訓練,有時候還會組織一些線下聚會。總得來說,Carless 表示,“這就是一個調查增幅器。”
Sankin 覺得現階段的初步成果只是揭開了無限可能性的面紗而已,它的意義不僅僅在於幫助 Reveal 去跟進日益猖狂的仇恨行動,同時也吸收讀者的意見,塑造報道的走向。
“我擔任專題記者已經有十年了,我有相當牢靠的資源,我可以直接向他們諮詢。(但是)提問的那個總是我,”Sankin 說。吸收仇恨偵探團的志願者一起搜尋信息,他認為,“就好像同時舉起幾支火炬,把角落裡的勾當照得清清楚楚。”
這篇文章最初刊登於“會員制求索項目”。該公共研究項目聚焦會員模型,由荷蘭新聞平台 De Correspondent 和紐約大學 Studio 20 項目創辦。
 Melanie Sill 負責管理“the Membership Puzzle Project”的“Join the Beat”項目。她曾於多家媒體擔任首席編輯及新聞主任,包括KPCC/Southern California Public Radio, The Sacramento Bee, and The News & Observer of Raleigh。她還於北卡羅蘭納州進行獨立編輯與新聞顧問的工作。
Melanie Sill 負責管理“the Membership Puzzle Project”的“Join the Beat”項目。她曾於多家媒體擔任首席編輯及新聞主任,包括KPCC/Southern California Public Radio, The Sacramento Bee, and The News & Observer of Raleigh。她還於北卡羅蘭納州進行獨立編輯與新聞顧問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