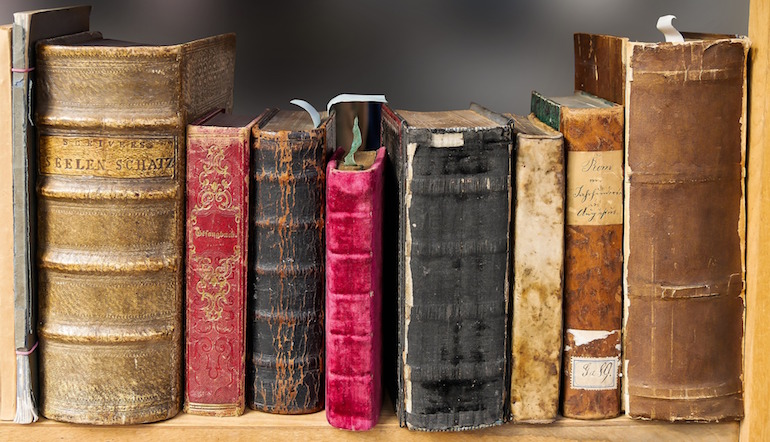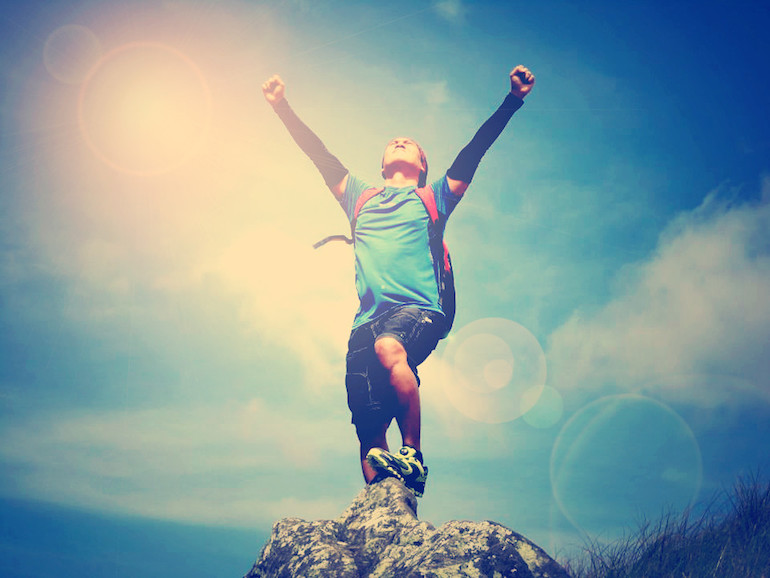講故事的方法數不勝數,值得被講述的故事也是一樣。一份調查報道可以是探尋問題的起因或者尋求解決辦法;也可以是揭露被隱瞞的不道德行為,或聚焦於一直發生在人們眼皮底下卻被忽略的議題;它既可以重點關照社會的某個角落,反映它的真實狀況;又或者給予這個群體發聲機會,更全面細緻地了解給他們帶來影響的困難之所在。根據故事類型的不同,你也許會採用不同的講述方式。
Christopher Booker 的《七種基本故事結構》(The Seven Basic Plots)一書為我們提供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框架。雖然書中探討的是虛構類文學的敘事手法,但在長篇調查類作品中你也同樣受用。
探索性敘述
探索型敘述(故事主人公探尋某種“獎品”)是調查報告中最常見的一種,因為作者很自然地帶着“對真相的探尋”的敘述角度。
然而這種追尋探求並非必須從作者角度出發:比如試圖給建制帶來改變的內部人士,一個告密者或任何一個人試圖爭取或揭露什麼(Booker 謂之“獎品”)的故事,都可以採取這種敘述方式。
書中也提到了,破解疑團的敘述模式,但它並不屬於七種基本情節。儘管它實質上也是一種對真相的探尋,但 Booker 認為仍需區別對待。
這種模式比較適用於講述如何尋求將真相挖到底的故事(尤其在雖然最終未能成功但過程卻非常豐富的時候,這一模式十分有效)。如果能預判到調查結果未必盡如人意,但挖掘到的信息個調查過程中遭遇的各種障礙有重大意義時,它會是個很好的後備選項。
斬妖除怪
雖然斬妖除怪的情節與探索性敘述近似,但不同之處在於這個模式中存在一個敵人。這個敵人既可以是抽象而模糊的勢力,也可以是具體的人,例如一位有虐童嫌疑的權勢之人。
這個“妖怪”可能在威脅着某個個人或地區(在新聞調查中可能是某個國家面臨財富流失或者偷稅漏稅;在故事裡可能某個小鎮遭遇有組織的犯罪或者環境破壞)或者甚至整個世界(一些關於環境變化或者核武器的故事關涉到全球面臨的共同威脅)。
舉例來說,一個律師接了個沒人肯接的案子,那麼這個故事的主題就是律師試圖代表他的客戶對抗這個體制。
“迷途知返”(同樣不屬於七種情節)也許是這種情節更加黑暗和反烏托邦的版本:
“主人公在故事的前半部分堅持自己是正確的,當權一方是錯誤的,隨着故事進展,他發現自己對現實的認知非常狹隘,而對方才是正確的。最後,主人公承認當權者的統治合法性。”
什麼故事屬於此類?也許是某個轉換立場或放棄抗爭的人?然而,因為這種模式含有潛在的宣傳意圖,所以它比起其他方式稍顯遜色。
白手起家
這種故事模式正如其名,可以用來講述一個人的發跡史。新聞調查中它很可能作為次要故事線存在,而在專題報道中,許多關於重要人物的生平簡介或訪談就經常屬於這個範疇。
悲劇
與白手起家相反,悲劇講述的故事往往是由高處跌落,尤其是因為某個具體的失誤(可能由於試圖掩蓋這個錯誤從而觸發一些列事件)而急轉直下的故事。
圍繞着“如何發生”這個問題展開的調查會經常使用這種故事結構:比如在格倫費爾塔火災或者英國建築業巨頭 Carillion 破產後,記者深入背景試圖調查導致事情發展至此的原因是什麼,而你會看到他們白紙黑字地用“悲劇”一詞來表述。
長篇報道《Boots 如何由藥房變成流氓的》一文是關於悲劇的精彩範例,它關注一家企業是如何與其創立人和其員工的初心與信念漸行漸遠的。
回歸
這是關於一場回歸的旅程,其敘事核心在於個體歸來的理由。
調查報道中出現的例子包括非法交易(被不實情況所誘惑而出發,發現真相後必須設法回頭);告密(謀得一份不錯的工作卻發現事情並非如此——電影《斯諾登》(Snowden)就是這樣一個例子);或者甚至是關於轉行的故事(足球運動員因傷病終止職業生涯,不得不返回家鄉從頭開始)。
我、Yemisi Akinbobola 與 Ogechi Ekeanyawu 合作完成的調查報道《追蹤金源》(Follow the Money)就是採用了這種敘事模式。這篇報道講述了一群充滿抱負的年輕尼日利亞足球運動員,是如何被轉送到至喀麥隆並在那裡被遺棄的。當我們獲得關於這一連串事件的資料後,馬上就意識到這種模式很適合這個故事。
重生
這種故事模式和回歸有相似的關注點——但它更接近於從某種形式的死亡中回歸,換句話說就是重生。某些情況下,“救贖”可能是個更好的措辭。
雖然白雪公主可能是最家喻戶曉的範例(她陷入沉睡一百年後才得以被一個王子喚醒),但《青蛙王子》或《美女與野獸》或許才是更好的例子:故事主人公分別受困於某種形式(青蛙/野獸),但通過某種方式獲得救贖並從困境中逃脫(獲得“重生”)。
從新聞報道的角度看,《聖誕頌歌》也許更有用:故事講述一個刻薄的商人經歷重生成為樂善好施之人,它重點着墨於這種轉變是如何發生的。
這種故事結構同樣有助於肖像刻畫及人物稿,在寫關於人物轉變的時候也可以使用。
《漏網之魚》(The Uncatchable)就是在報道中採用這種敘述模式:它講述了一個關於希臘頭號通緝罪犯如何成為綠林好漢的故事。
喜劇
喜劇的故事結構在新聞報道中較為少見,大概因為它一般對應的是非嚴肅性主題,並且/或者因為這種結構使主題顯得輕浮瑣碎。這裡的喜劇情節並非指故事內容幽默搞笑,而是指“事情不對頭”後又得以糾正。
莎士比亞喜劇是最佳佐證:故事裡充滿誤解,結尾時以婚禮告終。如果你曾聽過一個關於“錯誤的喜劇”(comedy of errors)的故事(這個名詞出自一部莎士比亞早期的喜劇),那你就會知道喜劇的故事結構可能有效——但注意不要使文章花哨造作。
合併情節
請記住一個故事也許會用到不同的故事模式。一名運動人士也許正開展他的探尋之旅,而在漫漫長路上可能會遇到一個又一個的“妖怪”。守財奴斯克魯奇的重生的故事不僅涉及他的發家史,也會講述飛黃騰達後的他如何撕毀與貝拉的婚約,這兩條線索都在《聖誕頌歌》中的一章中有所交代。
你需要分清主次,什麼是主要的故事線,而哪些是屬於次要的情節。
質疑情節
當然,這些不同的敘述模式只是為了幫助你更好地使用手頭材料,它並不意味着我們要將各種事實硬塞進與之不匹配的盒子里,或者歪曲事實。
比如,一個符合“白手起家”情節的故事並不會改變其本身內容;它僅僅幫助我們更好地與編輯溝通,並督促我們更仔細地思考文章的敘事結構以及故事所牽涉出的議題。
比如,你也許會聚焦於它“並非只是普通的白手起家的故事”或“她的旅途並非一帆風順”;你也許會去更批判地質疑白手起家是否是故事的唯一主題。
這種批判階段很重要。人類會自然而然地從噪音(包括隨機偶然的聲響)中總結模式,而記者更是專業的模式創造者:不同的事件被組織排列、去蕪存菁,使之更好地被理解。
因此,清晰直接地思考故事形式有助於我們更進一步,並檢驗自己是否下意識地採用這些形式。
一旦你意識到了自己有傾向採取某種故事類型的敘述方式,那就需要向自己發問,包括:
• “妖怪”是否真的是妖怪——它是如何成為妖怪的?(也許它自己也處在某種探尋的旅程之中?)
• 探尋必然是好的嗎?(答案是否定的)它會帶來什麼非預期的後果?
• 在“回歸”的敘事模式中,你是否掌握了所有信息解釋某人踏上歸途的動機?
• 是否有人在掩蓋信息以使故事看起來像是“白手起家”?
• 他們是否真的“重生”了?
• 失敗者自然會是悲劇的焦點——但是否也有從悲劇里獲益的一方?
究其所以,這正是敘事模式最重要的價值之一:通過將我們不由自主地傾向採用(以及那些我們圍繞其談論)的敘述方式外化具象出來,有助於我們發現自身存在的盲點。
本文首發於 Paul Bradshaw 的博客,全球深度報道網或授權轉載。
 Paul Bradshaw 在伯明翰城市大學的數據新聞學與跨平台移動新聞學教授研究生課程,獨立及合作出版關於線上新聞業以及互聯網的書籍與章節,包括《線上新聞業手冊》、《從電子表格中挖掘故事》、《數據新聞盜竊》和《新聞數據收集》。
Paul Bradshaw 在伯明翰城市大學的數據新聞學與跨平台移動新聞學教授研究生課程,獨立及合作出版關於線上新聞業以及互聯網的書籍與章節,包括《線上新聞業手冊》、《從電子表格中挖掘故事》、《數據新聞盜竊》和《新聞數據收集》。